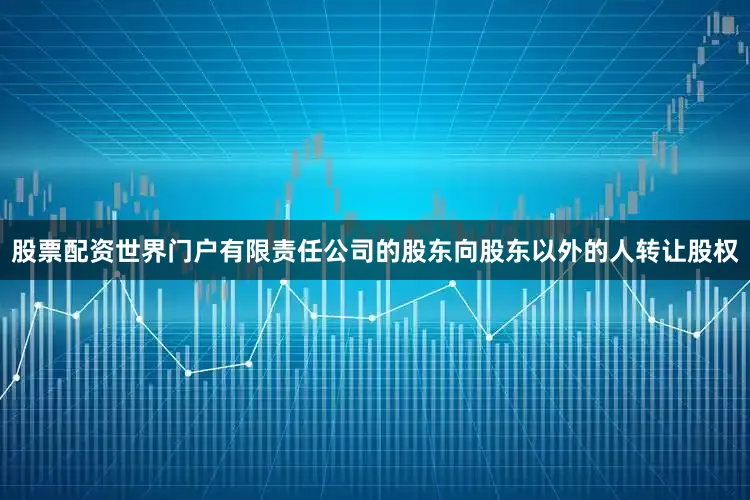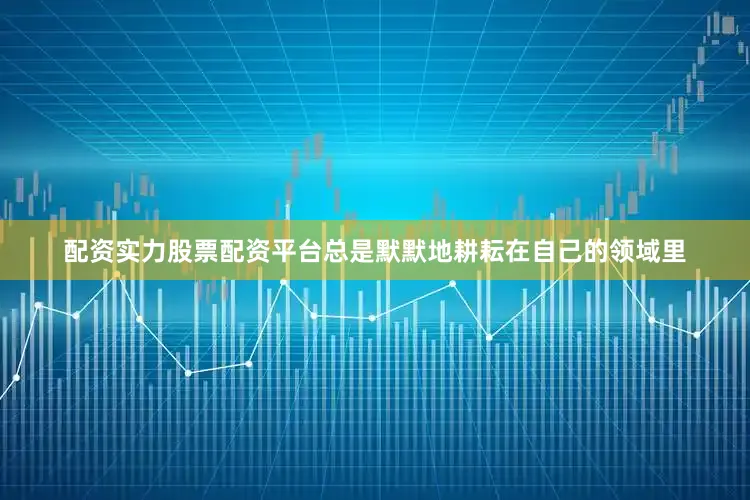汉武帝建元三年(前 138 年),长安城西郊的渭水岸边,一支百余人的队伍正整装待发。为首的青年郎官身着粗布汉服,腰间佩着汉武帝亲赐的符节,他便是张骞。这位年仅二十七岁的使者,即将踏上一条前所未有的征途 —— 穿越匈奴控制的河西走廊,寻找被匈奴驱逐的大月氏部落,联手夹击强敌。谁也未曾料到,这趟使命竟会耗时十三年,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传奇的探险之旅。
草原囚笼中的坚守
队伍出陇西后不久,便在河西走廊被匈奴骑兵包围。张骞与随从堂邑父等人全部被俘,押往匈奴王庭(今蒙古国境内)。军臣单于得知他们要去联络大月氏,冷笑说:“月氏在吾北,汉何以得往?使吾欲使越,汉肯听我乎?” 虽未处死他们,却将张骞软禁起来,还强行给他娶了匈奴女子为妻。
在匈奴的岁月里,张骞表面上逐渐 “归化”,甚至有了孩子,但那根象征使命的符节始终被他珍藏在怀中。每当夜深人静,他总会摩挲着符节上磨损的牦牛尾,遥望南方的汉地。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十年,匈奴人渐渐放松了警惕。元光六年(前 129 年)的一个深夜,张骞趁匈奴人狩猎狂欢之际,带着堂邑父和妻子,悄悄逃出了监视圈。他们没有选择返回长安,而是继续向西,朝着最初的目标大月氏进发。
展开剩余68%穿越流沙的绝地求生
离开匈奴控制区后,张骞一行闯入了一片荒无人烟的地带。这里便是后来被称为 “白龙堆” 的罗布泊荒漠,夏季烈日当空,地表温度高达五十摄氏度,脚下的流沙会随时吞噬生命;冬季寒风如刀,夜晚气温骤降至零下二十度。他们用皮囊储存雨水,靠堂邑父射猎的鸟兽充饥,有时一连数日找不到水源,只能咀嚼干燥的皮囊碎屑解渴。
在翻越葱岭(今帕米尔高原)时,队伍遭遇了暴风雪,一名随从失足坠入冰缝。张骞拉着他的手坚持了半个时辰,最终只能眼睁睁看着同伴消失在皑皑白雪中。当他们终于抵达大宛(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)时,百余人的队伍只剩下张骞和堂邑父两人。大宛王早就听说过东方汉朝的富庶,热情款待了他们,还派向导护送他们抵达康居(今哈萨克斯坦境内),再由康居人转送至大月氏。
使命未竟的归途
然而此时的大月氏已在阿姆河流域定居,这里土地肥沃,远离战乱,国王早已无意东返复仇。张骞在大月氏停留了一年多,虽未能达成联盟的目的,却详细考察了当地的风土人情、物产气候,还了解到西南方向还有一个名为 “身毒”(今印度)的国度。
元朔元年(前 128 年),张骞决定返程。为避开匈奴势力,他选择从南山(今昆仑山)南麓穿行,不料在羌人居住区再次被匈奴俘获。这次扣押又持续了一年多,直到军臣单于去世,匈奴内乱,张骞才带着匈奴妻子和堂邑父趁机逃回长安。
元朔三年(前 126 年),当衣衫褴褛的张骞出现在长安街头时,几乎无人能认出这位昔日的青年郎官。十三年间,他从青丝到白发,出发时的百余人仅存两人,但他手中那根符节虽已磨得只剩光秃秃的竹竿,却依然挺立如初。汉武帝在未央宫亲自接见了他,当张骞献上西域地图,讲述大夏(今阿富汗)的汗血马、安息(今伊朗)的银币、条支(今伊拉克)的驼鸟时,满朝文武无不惊叹。
凿空西域的千年回响
张骞带回的信息,彻底打开了汉朝人的眼界。元狩四年(前 119 年),汉武帝再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,这次他率领三百人的庞大使团,携带上万头牛羊和大量金币丝绸,顺利抵达乌孙(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),并派副使分赴大宛、康居、大月氏、安息等国。从此,中原的丝绸、瓷器沿着这条通道源源不断运往西方,西域的葡萄、苜蓿、佛教也随之传入中原,“丝绸之路” 正式形成。
元鼎三年(前 114 年),张骞病逝于长安。他生前未获显赫爵位,死后却被封为 “博望侯”,这个称号意为 “广博瞻望”,恰如其分地概括了他的历史功绩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称他的壮举为 “凿空”—— 如同在未知的荒漠中开辟出一条大道。
如今,在新疆库车的克孜尔石窟中,仍保留着一幅描绘张骞出使西域的壁画,画中的他手持符节,眼神坚毅。两千多年来,无数商队、使者、僧侣沿着他开辟的道路往来穿梭,而张骞那十三年不改初心的坚守,早已超越了时代,成为中华民族探索未知、开拓进取的精神象征。正如历史学家翦伯赞所说:“他是一个冒险家,又是一个天才的外交家,同时又是一员战将,真可谓中国历史上出类拔萃的人物。”
发布于:重庆市汇盈策略-靠谱股票配资门户-广西股票配资一览表-配资门户网站平台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